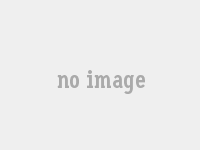学取鸱夷泛钓船读音(范蠡钓鱼经验学取鸱夷泛钓船?)
1.
对于宋江走招安路线的争论时常出现。这种因世界观不同而产生的差异,估计永远不会结束。那么,这种争论何时产生的呢?
从《水浒传》诞生之日起,就产生了这种争论。拿出证据给大家看看:
之一:
莫把行藏怨老天,韩彭当日亦堪怜。一心征腊摧锋日,百战擒辽破敌年。
煞曜罡星今已矣,谗臣贼相尚依然。早知鸩毒埋黄垠,学取鸱夷泛钓船。
之二:
生当鼎食死封侯,男子平生志已酬。铁马夜嘶山月暗,玄猿秋啸暮云稠。
不须出处求真迹,却喜忠良作话头。千古蓼洼埋玉地,落花啼鸟总关愁。
上面两首结束诗在百回荣与堂本,和后期的百二十回本中都出现了。第一首诗表露出对梁山集团覆灭的惋惜之情。很显然,此诗的作者是反对招安的。所以,他说,星宿已经消失了,奸臣还活得好好的。早知道有毒酒,不如去钓鱼呢。
第二首诗则没有任何惋惜之意。它的重点是“志已酬”!人生的志向已经完成了,何必在乎结果呢?即便是喝了毒酒,也是“千古蓼洼埋玉地”。有才华的人,为国献身的人,千古留名!
两首诗体现了两种思想和两种境界。甚至说,这两种思想是有矛盾冲突的。很难相信这两首诗,出自同一位作者笔下。
当然,这是我这种没文化人的短视。曾有某教授,在阐述水浒传的思想过程中,分别引用了这两首诗中的句子。在他眼中看来,这两首诗好像既没有违和感,也没有冲突感。因其在学术界较有权威,并且,在分析征辽的伪作方面很能说服我,让人心悦诚服。所以,导致本人的自信遭受严重打击。
好在本人脸皮厚,即便错了,也想表达自己的观点。——这两首诗,不可能是一个作者所为。
个人认为,第二首诗,百分百的是施耐庵先生的原著。因为“不须出处求真迹,却喜忠良作话头。”此句的内容,包含了书中两位重要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变化。可以认为,第二首诗,是作者给两位重要人物做出的思想总结。正因如此,这首诗必然是施耐庵先生的亲笔。
若是不了解书中主要人物的行为,很难读懂这首诗。谁更了解书中人物呢?当然是作者本人。
说到此处,顺便驳斥一些“多名作者”说。驳斥之前,先说结论:百回容与堂本,除中间攻辽部分以外,其余部分,大体是施耐庵先生所为。
为啥说是“大体”呢?因为有后人把《水浒传》当成猪肉,往里面注水。
2.
小说开始出现的第一个结构性的重要人物是高俅。他的人生经历代表了整部小说的背景。有了黑暗的背景,才有飞蛾扑火追求光明的悲剧。
第二个出场的主要人物,是与梁山没有任何瓜葛,最后消失的王进。这个人物绝对不是仅仅为了串联出史进的龙套。因为,作者可以虚构任何人物当史进的老师。那么,这个人物存在的意义何在?
许多读者喜欢把王进与林冲做对比。因为他们的身份相同,必然会让读者思考他们不同的人生。王进,面对即将到来的迫害,飘然而去。林冲,面对迫害措手不及,家破人亡。这样的对比无可非议。不过,毕竟对比的是个人的遭遇与命运。若是放在整个民族与社会当中来看,却是微不足道的类比。
中国人从古到今,都有崇拜隐士的思想。这种思想在民间非常有市场。这些隐士的认识和行为大多都是这样:朝廷太黑暗,老子有本事,但是,不陪你们玩。王进在《水浒传》中就是这种隐士的典型。
作者之所以,把这种隐士思想的人物,放在小说早期出场,其实,是为了与小说最后的结尾,“生当鼎食死封侯,男子平生志已酬”,进行整部作品的前后照应和对比,来取得强烈的反差艺术效果。
隐士的思想,最终保存了自己。但是,他们却弃社会和民众的未来于不顾。他们心中只有小我,没有国家社稷和民众。
宋江这一类人努力去改造社会。明知朝廷黑暗、社会黑暗。但是,为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进步,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,宁可献出自己的生命,而初衷不改!
作者利用王进的隐士思想为代表,为整部书的主人公,做出了结构性的铺垫和思想上的对比。这样前后的对比,是中国人对社会认知的对比;是人生观的对比;是社会不同思想的对比。
李卓吾最后评道:“天下哪有强盗生封候而死庙食之理?”是的。强盗当然不会死后封侯。但是,当他们最后改变了强盗身份,为国尽忠而死,怎么不能“死庙食”?李卓吾不懂得“志已酬”的境界。
小说中最早描写的高俅和王进,是作者做出的重大的结构性安排。用这样的布局,来照应整部小说的发展,和主人公最后的结局。这种精心设计的结构,怎么可能是多名作者的巧合?
抛开艺术欣赏和作品的思想,而判断作者,恐怕是钻牛角尖了。
3.
整部小说不仅思想统一协调,包括对所有的主要人物,都进行了前后照应的写法。比如,鲁智深在书中第三回就出现了。而作者在小说的结尾,通过对小说素材的取舍和重大改动,照应了鲁智深和武松的整体人物形象,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差别。这样的做法,怎么可能是多位作者所为?
整部小说的人物塑造手法,小说写作技巧,素材的选用方式,人物矛盾的制造,情节的推动,甚至,忽悠读者的方式,都是统一风格的。怎么可能是多位作者所为?
关于写作技巧和素材等问题,占用篇幅较多,暂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。本文的重点是想提示朋友们,注重小说最后的“之二”结束诗。因为这首结束诗是整部小说的点睛之笔。里面不单包含小说主要人物的言行和思想,还体现了作者在整部书中反应出来的思想以及人生观。
若是读懂了这首诗,多名作者的设想,根本无法成立。
用小说中的人物出场诗之有无,以及某情节人物的出现,或者某诗词与他人作品相同.....等等,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,怎么能够作为判断作者,是否为同一人的证据呢?恐怕有捡芝麻,丢西瓜的嫌疑。
忽视小说的整体结构、写作手法、以及体现出来的思想,不是欣赏小说的态度。
4.
不过,小说结尾的“之一”诗就很滑稽。显然是后人强行安插进去的。因为,他不仅提到,“百战擒辽破敌年”。而且反应出来的思想,与作者的思想完全相左。何况,它还有一个最滑稽之处——“学取鸱夷泛钓船”
“鸱夷”二字,应该指的是范蠡。他后来给自己起个号,叫鸱夷皮子。
但是,......重要的事情,要强调但是......在范蠡之前还有一个典故,叫做“鸱夷浮江”。
这个典故讲的是,伍子胥被吴王夫差冤杀,尸体被鸱夷革包裹后扔到江里。——伍子胥可不是去钓鱼。他是被喂了鱼!
作为同一时代的人,说范蠡不了解伍子胥的悲惨故事,恐怕说不过去。而范蠡给自己起这样的号,到底是什么心态?虽然今天无法了解,但是,伍子胥的故事在前,范蠡的故事在后。“鸱夷浮江”的典故在前,“鸱夷皮子”的典故在后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写诗,使用的典故字眼与前人典故重叠,并且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含义,还不够滑稽吗?
所以,百二十回的结尾把这首诗改成——“早知鸩毒埋黄壤,学取鸱夷范蠡船”。改写者明确解释了一下,此鸱夷,是范蠡,不是伍子胥。
本人不懂诗词,无法确定“鸱夷范蠡”这两个名词并列是否合适。但是,我能确定,这是一首用典不准确的烂诗。怎么改,都是烂诗。尤其改烂诗的后人,以为自己弥补了前人的缺陷,是很聪明的做法。其实,他们不知道自己更滑稽!
因为他们缝补的东西,是注水猪肉里的水!
可以反对宋江的招安,可以批评施耐庵的思想。但是,把这种烂诗放在小说最重要的位置上,偷偷摸摸的塞入《水浒传》中。意欲何为?
有些不法商人为一己之利,把猪肉或牛肉注水增加分量之后再去贩卖,完全不顾消费者的利益和健康。而中国的一些文人的品行,比这些缺德的不法商人有过之,而无不及。因为我搞不懂,他们这么做有何利益?
施耐庵的棺材板,居然还能盖得住。也算是宽宏大量。